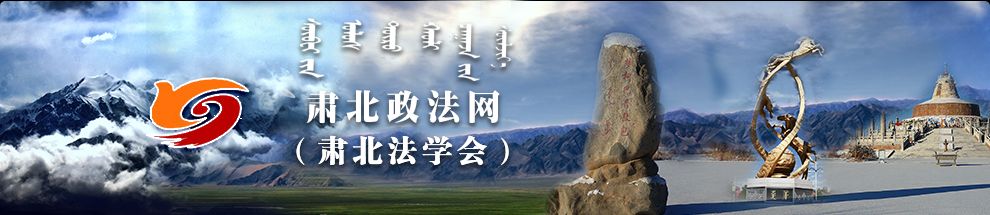天边的苹果
看到它我就想到了在那个离天最近、离家最远的地方——
天边的苹果
□聂虹影
家里的茶台上,放着一个苹果,那是一个普通的苹果,小小的,红绿相间,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,给它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,若有若无的清香弥散在空气中。它来自遥远的西藏阿里,随我横跨大半个中国来到北京。
到达阿里时,是正午时分,尽管当地的同事介绍说这是一天中空气含氧量最高的时刻,尽管先是从北京飞拉萨,有一个晚上的缓冲时间,第二天才飞阿里,可下了飞机,依然有心慌气短的感觉。车上有氧气,一路吸氧到达阿里边境管理支队机关所在地。
支队营区是一片平地,像所有的部队营区一样,干净、整洁。尽管承载着办公楼、宿舍楼、公寓房……但偌大的院子依然显得空旷寂寥。围墙外就是山,光秃秃的褐色的山,背景是湛蓝的天、洁白的云。这场景,以前在内地的舞台布景画面里见过许多次,在没来阿里之前,一直认为这个背景好假啊,完全是道具的感觉。到了阿里,看到蓝天白云衬托下褐色的寸草不生的山,才知道原来不是布景假,而是我从来没见过真景。营区内也有绿色,手指粗细的树,也有花,零星的几朵,淡粉、浅紫、是生长在高原的格桑花,还有草,也是稀稀落落的,这一小撮那一小撮。同行的民警介绍说,这里是高寒地区,植物很难存活。
食堂工作餐后,准备出发去派出所调研。等着集合登车时,一名民警跑过来,手里举着一个苹果,递给我说,“你尝尝,这个苹果特别特别好吃,洗干净的,你快尝尝。”递给我后转身就走开了,我还没反应过来,还没想好拒绝还是接受,也没来得及询问或者听人介绍他的名字,甚至没来得及看清面孔,他就走开了。
我捧着它,觉着真是一个漂亮的苹果,红色和青色相间。旁边的同事告诉我,这是阿里自产的苹果,来自阿里最西的札达县。
在阿里,能吃上非塑料大棚里种出来的本地苹果,真是没有想到。同事介绍说,由于树木对水分、热量的要求高于其他的灌草植被,而这里高寒缺氧干燥的气候,无法供给树木生长所需的基本热量,树木很难存活。他指着车窗外说,这里到处都是荒山秃岭,长棵草都很困难,所以能够长出苹果确实是高原的奇迹。
苹果的产地,阿里最西的札达县,那是青藏高原最年轻的一块陆地。那里除了延绵不绝的荒原,还有一个巨大的峡谷,叫萨让峡谷。罕见的绿地就位于萨让峡谷,栽种果树,果树开花,花儿结果……内地最常见的苹果,在人们的悉心照料下奇迹般地生长。这里的苹果,酸甜可口,回味悠长。只是苹果的运输,需要经历无比艰险和漫长的旅程,山高路远,弯连弯,拐连拐,连绵不断的深川巨壑,令人望而却步,只有走过那段路的人,才会真正理解。那里每年只有夏季短短几个月能和外界联系,其余时间与世隔绝。有人说“没到阿里,就没到过西藏;没到札达,就没到过阿里;没到萨让,就没到过札达。”
得益于组织的关怀,现在各种保障都很到位,食堂的伙食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水果,苹果作为抗折腾、能储存、维生素含量又丰富的水果,餐桌上自然缺不了,但基本上都是内地或者新疆产的苹果,阿里的苹果由于生长艰难,产量又少,加上运输困难,因此显得珍稀而珍贵,平时很少能见到和吃上。这个同事从哪里弄来的,放了多久,我无从知道。只知道他把这份珍稀珍贵给了我,他甚至没有想着让我知道他是谁,只是想着让第一次来阿里的我尝尝,也许这是他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。
听了这番介绍,更觉这个苹果的珍贵,我把它用餐巾纸包好了,放到信封里装到随身背的包里,此后的日子,它陪着我下乡、吸氧、调研,陪着我聆听民警们的故事,感知和见证民警们的奉献和辛劳,陪着我感动、流泪,陪着我踏上归途,在数千米的高空穿行,最后回到北京。
那个苹果,一直放在客厅的茶台上,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,沐浴着北京的阳光,也感受着窗外城市的繁华。时间一天天过去,它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光泽,开始有了褶皱,最后枯干成小小的一团,看不出本来面目,我依然没舍得扔掉,就这么摆放在茶台上。看到它我就想到了在那个离天最近、离家最远的地方,那里的群山、蓝天、白云,那个守护国门边境、默默奉献付出的群体。
(作者单位: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中心)